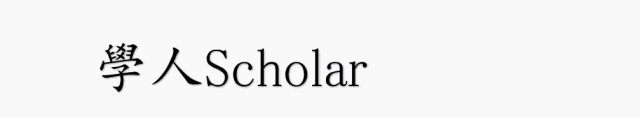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李伯重先生,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1949年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85年获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尔后在密歇根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先后任职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并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理工学院、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
*文章节选自《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代结语”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个看法代表了“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先进思想家对中国历史的激烈批判,从今天来看或许有些过激,但是确实揭示了一个事实:历史并不只有光明的一面,而且还有黑暗的一面。一个人如果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方面,那么他对历史的理解就是不全面的。
以往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在谈到历史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总是谆谆教导读者说: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的历史都充满友谊。即使彼此发生战争,也被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兄弟阋于墙”;战争之后,“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大家又成了好兄弟,继续共同谱写友好的新篇章。这种说法自然是表达了历史的“主旋律”,然而一切事物都有两个方面。各国人民交往的历史,既有铺着鲜花和红地毯的光明一面,也有流淌着血水和眼泪的阴暗一面。正因为历史有这样的阴暗面,所以布罗代尔说,以往的一切历史从来没有公正可言。以建构世界体系理论著称的沃伦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也说:“(历史)书写真的是可怖的。”本书所讲的故事中,有一些就反映了历史的这一面。布罗代尔说:“作为历史学家,我的任务既不是要判断资本主义的好坏,也不是要认定它守规矩或玩花招,而是要认识它或理解它。”对于早期经济全球化,我在此也不是判断它是好还是坏,而只是要认识它或理解它。既然这段历史有今天我们看来阴暗的一面,那么我们就应当正视之,这样才能认识它或理解它。
火枪加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经济全球化开始并迅速进展,导致东亚世界原有的秩序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又尚未建立。因此如同整个世界一样,东亚世界也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混沌天地。在这个混沌天地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国际行为准则。什么人类之爱、公理正义、礼义廉耻等,在这里都看不到踪影。这里经常能够看到的是刀光剑影,听到的是枪炮轰鸣。而隐藏在其后的,除了传统的征服、掠夺和奴役外,更多的是商业利益。
西方的司法女神,披白袍,戴金冠,左手持天平,右手持长剑。这个形象来自古罗马神话中的正义女神朱蒂提亚( Justitia),英语中的“ justice”一词就来源于此。如前所述,近代早期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形象是“左手拿着账册,右手拿着刀剑”。考虑到这个时期发生的军事技术革命,我们可以把刀剑改为火枪。火枪意味着新型暴力,账簿意味着商业利益,因此“火枪加账簿”就是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的写照。其含义是这个时期蓬勃发展的国际贸易与暴力有着程度不等的联系。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各种利益主体在相互交往中往往运用暴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原因是出于商业的性质和商人的本性。商业是一种有组织的为顾客提供所需的商品与服务的行为,通过以高于成本的价格卖出商品或服务来盈利。盈利是商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动力。这种性质体现在从事商业的人(即商人)身上,因此商人的本性是求利。在求利的驱动之下,商人常常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古希腊哲人柏拉图这样评论商人:“一有机会盈利,他们就会设法谋取暴利。这就是各种商业和小贩名声不好,被社会轻视的原因。”另一位哲人亚里士多德也说:
“(商人)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货以谋取自己的利益,这是不合自然而且应该受到指责的。”古罗马政治家和学者西塞罗更认为商人是卑贱的、无耻的,因为他们“不编造一大堆彻头彻尾的谎话就捞不到好处”。
在古代的东亚世界,商人也因唯利是图、重利轻义而备受指责。唐代诗人元稹在《估客乐》诗中,对当时商人的唯利是图、重利轻义做了生动的描述:
估客(即商人)无住著,有利身则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莫所避,求利无不营;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但交假,本生得失轻;自兹相将去,誓死意不更。亦解市头语,便无乡里情。
正是这种贪欲,驱使商人不惮风险,走遍天涯海角:
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
到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经商求利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由于国际贸易空间空前扩大而共同游戏规则尚未建立,商人贪婪的本性在这个广阔无垠同时又无法无天的天地里更加暴露无遗。为了利益的最大化,他们无所不用其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登宁的话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 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 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 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 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 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这段话也是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商人的绝佳写照。
这种对于商业利益的狂热追求,使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汪直等人会背弃父母之邦,成为倭寇首领;为什么郑芝龙在明朝、日本、荷兰之间纵横捭阖,今日是友,明日为敌;为什么一些“兄弟之邦”,一转眼就反目成仇,成为刀兵相见的敌人。这些现象背后就是一个词:利益。正如 19世纪英国首相巴麦尊( Henry John Temple, Lord Palmerston)所言:“一个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A country does not have permanent friends,only permanent interests.)在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东亚世界,情况就是如此。
“恶创造历史”: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历史发展的动力
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东亚世界的“火枪加账簿”,导致了诸多在今天不能容忍的恶行的出现和滋生。但是这里要说的是,这些恶行不仅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也是经济全球化赖以出现和进展的必要条件。换言之,这种恶乃是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发展的动力。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早在 19世纪初,黑格尔就已提出了这个观点。他在《历史哲学》中说:“我现在所表示的热情这个名词,意思是指从私人的利益、特殊的目的,或者简直可以说是利己的企图而产生的人类活动——是人类全神贯注,以求这类目的的实现,人类为了这个目的,居然肯牺牲其他本身也可以成为目的的东西,或者简直可以说其他一切的东西。”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这个观点大加赞同,说:“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恩格斯进而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制度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不仅如此,恩格斯还认为这种贪欲是文明社会赖以出现的原因:“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马克思在《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也引证英国学者曼德维尔的一段话并给予高度评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称之为恶的东西,不论道德上的恶,还是身体上的恶,都是使我们成为社会生物的伟大原则,是毫无例外的一切职业和事业的牢固基础、生命力和支柱;我们应该在这里寻找一切艺术和科学的真正源泉;一旦不再有恶,社会即使不完全毁灭,也一定要衰落。”正是在这种道德上的“恶”造就了早期经济全球化,它借“火枪和账簿”,把世界各地人民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就是“恶创造历史”的具体表现。
那么,这种情况是否就是命定而不可改变的呢?我的回答是:虽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在某一个时刻,历史发展面临多种可能的道路,而非仅只有一条道路。否则,我们就将陷入历史宿命论的泥潭了。由此出发,我们来看看在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东亚世界,是否有可能建立一种得到各方接受的国际秩序呢?
很显然,这种国际秩序不可能由私人机构或者社会团体建立,而只能由国家建立。道理很简单,因为国家是所有社会组织中最强大的。著名社会学家蒂利指出:因为国家控制着“毁灭手段”这种最极端的力量,因此国家可以被视为专门的、唯一合法的保护费勒索者。这个看法,对于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情况来说再合适不过了。如果国家不够强大,或者国家采取错误的政策,就会导致国际贸易无序化,而这种无序化的结果必然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国际行为准则。
早在其 1527年出版的《论商业与高利贷》中,马丁 ·路德(Martin Luther)就对欧洲国家在建立贸易的合理秩序方面的失职及其结果做了酣畅淋漓的描述:“现在,商人对贵族或盗匪非常埋怨,因为他们经商必须冒巨大的危险,他们会遭到绑架、殴打、敲诈和抢劫。如果商人是为了正义而甘冒这种风险,那么他们当然就成了圣人了……但既然商人对全世界,甚至在他们自己中间,干下了这样多的不义行为和非基督教的盗窃抢劫行为,那么,上帝让这样多的不义之财重新失去或者被人抢走,甚至使他们自己遭到杀害,或者被绑架,又有什么奇怪呢?……国君应当对这种不义的交易给予应有的严惩,并保护他们的臣民,使之不再受商人如此无耻的掠夺。因为国君没有这么办,所以上帝就利用骑士和强盗,假手他们来惩罚商人的不义行为,他们应当成为上帝的魔鬼,就像上帝曾经用魔鬼来折磨或者用敌人来摧毁埃及和全世界一样。所以,他是用一个坏蛋来打击另一个坏蛋,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没有让人懂得,骑士是比商人小的强盗,因为一个骑士一年内只抢劫一两次,或者只抢劫一两个人,而商人每天都在抢劫全世界。……以赛亚的预言正在应验:你的国君与盗贼做伴。因为他们把一个偷了一个古尔登或半个古尔登的人绞死,但是和那些掠夺全世界并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更肆无忌惮地进行偷窃的人串通一气。‘大盗绞死小偷’这句谚语仍然是适用的。罗马元老卡托说得好:小偷坐监牢,戴镣铐;大盗戴金银,衣绸缎。但是对此上帝最后会说什么呢?他会像他通过以西结的口所说的那样去做,把国君和商人,一个盗贼和另一个盗贼熔化在一起,如同把铅和铜熔化在一起,就像一个城市被焚毁时出现的情形那样,既不留下国君,也不留下商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引用了这段话,并且指出:“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罗马,后来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那里,情形都是这样。”
因此,倘若国家不能或者不愿来建立合理的贸易秩序,国际贸易就是一个丛林,而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就会成为强盗、窃贼、骗子。而上帝就利用魔鬼,假手他们来惩罚商人的不义行为。这正是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东亚世界所发生的情况。
置身新世局:晚明中国国家的责任与失败
导致“丛林法则”成为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东亚世界国际行为准则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东亚世界最主要的国家——中国,未能充分认识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在创建一种国际新秩序方面未能发挥积极作用。相反,面对蓬勃发展中的国际贸易和风云变幻的国家政治军事形势,明朝反应迟缓,行动不力,因此不仅未能充分利用新形势带来的机会,反而被新形势带来的挑战弄得焦头烂额,最后走向灭亡。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晚明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这一说法。2008年《河北学刊》与中国明史学会组织了“晚明社会变迁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专题讨论。在会上,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先生明确提出“晚明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的观点,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考察了晚明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结论是“中国早期近代化历程在晚明起步”。
史景迁用优美的文笔,对晚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做了如下描写:
在 1600年前后中国的文化生活繁荣兴盛,几乎没有国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如果枚举 16世纪晚期成就卓著的人物,比较欧洲的社会,不难发现,同一时期中国取得的成就在创造力和想象力上皆毫不逊色。
16世纪晚期,明朝似乎进入了辉煌的顶峰。其文化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城市与商业的繁荣别开生面,中国的印刷技术、制瓷和丝织业发展水平更使同时期的欧洲难以望其项背。
然而此时的中国却已充满危机,实际上是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1600年以后中国的情况,不仅与之前的繁荣和安定形成鲜明对比,更与西欧一些国家的发展背道而驰。正如史景迁所说:
“即使把这一时期看作‘近代欧洲’诞生标志已成共识,却很难视之为近代中国的明确起点。当西方驰骋全球,拓展视野,在探索世界的领域中独领风骚时,明朝统治者不仅禁止海外探险,丧失了认识世界的机会,而且自拆台脚,不到五十年就将自己的王朝断送于暴力。”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巨变?以往人们提出了多种解释,从万历怠政、魏忠贤专权等传统说法,到在“阶级斗争”史观和“资本主义萌芽”史观下提出的诸多观点,可谓多姿多彩。这些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立场:明朝灭亡是历史的必然。但是 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社会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在探讨帝国兴衰之时,最好能避免受到这样的诱惑,即在知晓帝国终有一日强大的情形下过早地寻找其强大的征兆,抑或在了解帝国终有一日灭亡的情形下过早地预测它行将崩溃。”虽然明朝灭亡的原因很多,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明朝当政者至迟从嘉靖朝就认清新的国际形势,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那么中国未必没有可能逐渐走向近代社会。
那么,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晚明中国为什么不能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呢?我的答案是:不仅中国未能选择另外一条路, 17世纪大多数国家也如此,因此中国的情况不足为奇。
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晚明中国所遇到的危机并非偶然,而是世界史上著名的“ 17世纪总危机”(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的一个部分。学界对“ 17世纪总危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在 17世纪,欧洲各国在政治、经济、宗教、外交等方面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集中爆发,表现为此起彼伏的政治革命、贵族叛乱、民族起义、宗教冲突、农民暴动及城乡骚乱,等等。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危机的表现形式和发展程度以及危机的内容、性质、进程、结果等都大不一样。在荷兰、英国等少数西北欧国家,政治改革和社会运动取得了胜利,建立起了有利于近代经济发展的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成为国际竞争中的胜利者。而其他国家则未能顺利渡过危机,因此在危机后的发展显然迟缓,其中诸如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先前的世界强权更日益衰落,成为国际竞争的失败者。
这次危机也存在于东亚世界。危机之前,中国、日本等国在经济上似乎都是一片升平气象,而到了 17世纪,中国的明朝崩溃了,日本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出现了“宽永大饥荒”。
在 17世纪 40年代,日本的食物价格上涨到空前的水平,许多百姓被迫卖掉农具、牲畜、土地甚至家人,以求生路,另有一些人则尽弃财物,逃至他乡,多数人生活在悲苦的绝望之中。由于白银产量大幅下降,日本的购买力受到严重影响。1635年,德川幕府禁止日本人到海外贸易,并于 1639年将葡萄牙人逐出长崎,还严格限制外国与日本的贸易。结果是许多富商严重受创,甚至有的在债权人的高压之下自杀身亡。经济衰退导致了社会动荡,爆发了日本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起义,即岛原大起义(亦称“天主教徒起义”)。幕府费尽周折,使用了骇人听闻的残忍手段才将起义镇压下去。面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幕府实行了新政策以改善民生,并颁布了一系列“节约和限制消费令”,遏制武士和商人阶层的奢侈行为,以此缓解被幕府视为“走投无路”的农民的负担。但在此时,日本的铜产量大大提高,提高了日本对华贸易的购买力,使得日本可以改善其经济。这些措施和情况,使得日本比中国更快地从“ 17世纪总危机”中恢复过来。但是这场危机也严重削弱了日本在东亚世界国际竞争中的相对实力,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为什么日本德川政权放弃了丰臣秀吉的海外扩张野心,而奉行一种闭关自守、“洁身自好”的政策。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明代中国未能通过这场危机,沦为失败者。继之而起的清朝,采取了若干措施,缓解了严峻的经济状况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得危机得以结束。到了 18世纪,中国从危机中全面走出,出现了新的繁荣。不过,因为这些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中国也未能像荷兰、英国等国家那样建立起一种适合近代经济成长的体制,从而为 19世纪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如果我们追溯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过程,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晚明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未能抓住机遇,从而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走上另外一条路。由于这个选择导致的“途径依赖”,使得中国不得不再等上两个世纪,才又在新的(或许是更为不利的)国际环境中,重新开始近代化的进程。这个曲折经历,令我们今天在读这段历史时感叹不已,也令我们深感肩上的历史使命,不能重蹈覆辙,再失去历史的机遇。
推荐阅读


赞 赏
往期精选
学人书单 | 36位学人荐书(文史哲) | 36位学人荐书(政经法) | 2018年学人Scholar编辑书单 | 东西方文化通识读本 学人访谈 | 易社强 | 伍国 | 萧功秦 | 杨福泉 | 何义亮 | 刘清平 | 姜克实学人往事&逝者 | 杨小凯 | 杨绛 | 扬之水 | 胡适诞辰127周年 | 高华逝世七周年祭 | 陈梦家 | 巫宁坤 学人史料 | 赵元任 | 钱穆 | 胡适逝世57周年 | 一瓣心香祭高华 | 一代文心 | 巫宁坤专题 | 余英时 | 苏东坡 | 打工诗人 | 四大发明 | 什么是自由 | 读书与思考 | 院系调整

学人·思想的芦苇
投稿、联系邮箱:isixiang@vip.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