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绣山中学2019暑期教师读书评比一等奖作品
被张扬的与被掩盖的
——读《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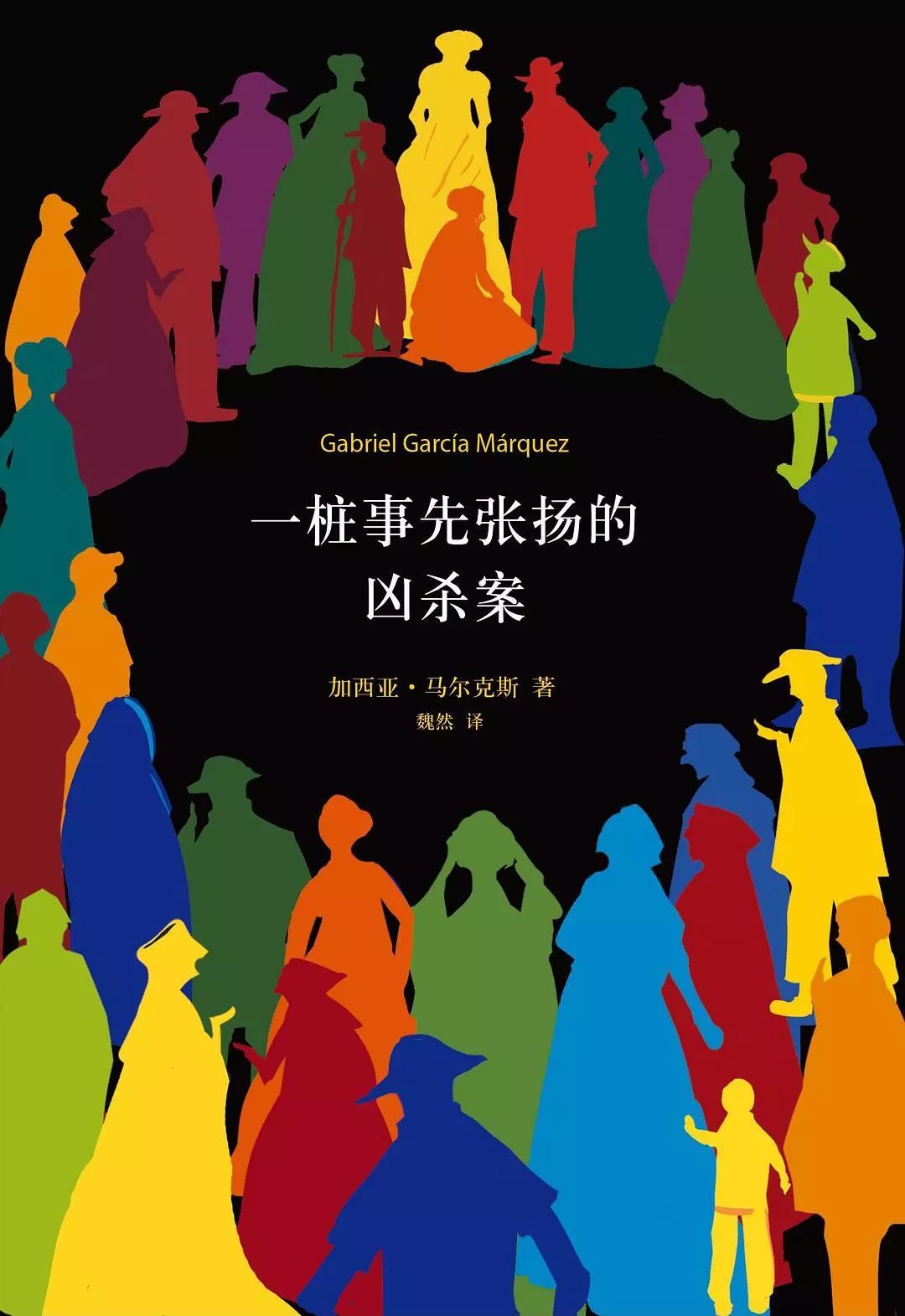
温州市绣山中学英语组 林若谷
谈到拉美文学,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百年孤独》。在九十年代的文艺界,马尔克斯的作品就像如今的村上春树小说一样,大受读者欢迎。然而那个时候,拉美作家(包括博尔赫斯)的书几乎都是盗版的,令人诧异是,盗版书的发行方大多是些官方出版社。为此,1990年马尔克斯访问中国时,随处可见的盗版《百年孤独》让他忿忿地留下一句话:“死后一百五十年都不授权中国出版我的作品,尤其《百年孤独》”。足见当时盗版之猖獗,也足见读者对马尔克斯的追捧,但追本溯源,当时马尔克斯的作品其实只被盗版两部:《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而他另外的所有作品压根儿没引起国人的半点关注,甚至至今如此,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这或许更让马尔克斯光火。因为他其他一些作品并不逊色于上述两部,其中就包括对马尔克斯作家生涯中起到至关重要,并直接促成其次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部中篇杰作:《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这是一本非常短小精悍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纪实味道,有些评论甚至将其定义为“纪实小说”。当然,“纪实文学”和“小说”之间是否不可草率逾越值得商榷,但我们无法否认源自于真实事件的创作,其猎奇魅力如同吃瓜群众对于爆料的垂涎。《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故事原型就来自于一个真实的事件:1951年1月的一个上午,马尔克斯的朋友兼义兄卡耶塔诺在众目睽睽下被奇卡兄弟杀死,而全镇人民几乎都已早早得知要他将要被杀。这件事情深深影响了马尔克斯后来的写作意识,直到30年后,他回到家乡,寻访了案件的亲历者们,以极尽还原事实本相的态度讲述了这桩离奇和荒唐的案件。然而,他并没有将这个故事写成悬疑推理或者是他擅长的魔幻现实主义,而是以一个记者冷静和客观的手法层层剖析,用一个个目击者的详实讲述将读者一步步引向那个案发的现场,让人真切感受到那个悲剧发生的上午。
故事非常的简单:小镇上有一位美丽的新娘,嫁给一个外乡来的新郎。但却在新婚当夜被退婚了。回家后的新娘在遭到家人逼供后,说是主人公圣地亚哥·纳萨尔玷污了她。于是,新娘的两位孪生哥哥怒不可遏,开始在小镇上游荡并散播要杀死主人公纳萨尔的消息。直到第二天上午,几乎全镇人民都知道了这个消息,甚至包括主人公的母亲、仆人和未婚妻。而主人公在次日上午也陆续遇到了这些人,然而就是没有一个人告诉他这个消息,也没有人去阻止那两个到处扬言要杀人的兄弟。直到双方在广场上相遇,主人公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乱刀杀死。
由此,吃瓜群众们都发现了,这个简单的故事里面疑点很多。比如新娘为什么被退婚?真的是主人公玷污了新娘吗?杀人者为什么要到处声张呢?为什么没有人告知主人公呢?等等。
这一切的疑问,都是马尔克斯在30年的时间里不断思考和寻访的,现在他在书里给出答案了吗?我不知道,只有靠你自己去解读了。
解读的方法,就是跟着作者去聆听小镇上每一个亲历者的叙述。对于众多人物的讲述,马尔克斯采用了环形结构,小说开篇第一句:“圣地亚哥·纳萨尔被杀的那一天,清晨五点半就起了床,去迎接主教乘坐的船。”(引自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这种开篇极其精巧,用一句话就将整个故事的开头(清晨出门)和结尾(主角被杀)讲完了,后面所有人的讲述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个一头一尾来展开的。忽而是讲述主角上午出门后的行踪和经历,忽而是讲述被杀前的活动和情感,以及杀人者兄弟俩的行踪和对话,貌似零碎的片段一环环拼接成完整且丰满的凶杀故事,就像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悬疑电影《记忆碎片》一样,以短暂失忆者的记忆碎片逐渐重整出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那么,这样貌似破碎的叙事手法读起来费劲吗?众多的人物和讲述会不会太过凌乱或冗长?
不会。这种写法的一个比较明显优点就是悬疑感很强。你会发现,书中每一个叙述者本身都带着强烈的疑问,因为每个人的记忆都是不完整的,所以他们也在质疑,在自我怀疑和怀疑其他人的意图,于是尽管案情早已昭然天下,但神秘感却经过作者的采访越来越浓郁。
更加高明的是,马尔克斯还在环形结构之上采取了双轨叙事,一条轨道是亲历者们的回忆和描述,另一条轨道是作者以采访者的视角去揣度这些亲历者当时的心态,这就像侯孝贤的电影,既有角色通过场面调度的形式展现情节发展,又有导演以文字旁白的形式表达故事内核。因此,越是读的深入就越会轻松明了。但是,作者当然不希望你完全依赖于他的判断,所以在最后他会卸下解说者的任务,而将你带入一种不得不思考的状态。
抱着上述那些疑问,我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查了一些资料,大多是说作者企图表达“民众的集体无意识”或者“被杀者命运的神秘性”之类的论断。但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聊聊,为什么小镇的人们对于杀人者的扬言显得无动于衷?
严格上来讲,小镇上人们并不属于那种典型意义上的“看客”,他们并非麻木不仁、见死不救,他们大多声称是由于不相信孪生兄弟会真的杀人,所以才没有告知主人公。这一点,是可信的。只是这种不相信杀人的心理背后却是源于一种隐匿不自知的怯懦,骨子里还是怕惹上是非,也怕激怒孪生兄弟真的去杀人,所以努力让自己确信他们不可能有胆量杀人。这种心态就小镇上居民而言具有普遍性,从小镇被采访的所有人乃至镇长的对话便可知之。而怯懦的产生不是意外和突发的情绪,是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的,这要与拉美民族作为殖民者后裔的那种孤独感和无奈性联系起来。
在南美洲,相当一部分的民众,对于民族概念是模糊的。一方面,他们是在拉美的土地上繁衍生息,这是他们的家园,他们热爱那片土地,对当年欧洲殖民者的掠夺和破坏愤恨不已。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又是西班牙等殖民者的后裔,是混血儿,是殖民者的遗弃儿,他们说着西班牙语,使用他们的文字。在文化认同上,他们又不由自主的受到欧洲甚至那些侵略者父辈们的深度影响。所以,他们的民族归属感是模糊的,如果他们反抗沙文主义,那么首先要反抗自己的身份,说到底要否定自己。这种矛盾和民族感的缺失,造成他们的自卑与怯懦。体现在个体上,就是既不信任自己,也不信任别人,集体孤独和无力。所以,小镇的人们才会认为孪生兄弟根本没有胆量去杀人,也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去阻止别人杀人。甚至于连杀人者也一样表现出了这种怯懦和无奈。马尔克斯借牛奶店老板娘的话,表达了这种心态:“她敢肯定维卡里奥兄弟并不急于复仇,而是迫切地想找一个人出面阻止他们行凶。可是阿庞特上校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所以,这场悲剧并不是个体的悲剧,而是拉美民族的精神悲剧。这或许也是拉美作家普遍想表达的一种内在问题吧。
所谓杰作,往往都是以精悍的语言,道出了最宏大的精神世界。

长按二维码
敬请关注 温州市绣山中学